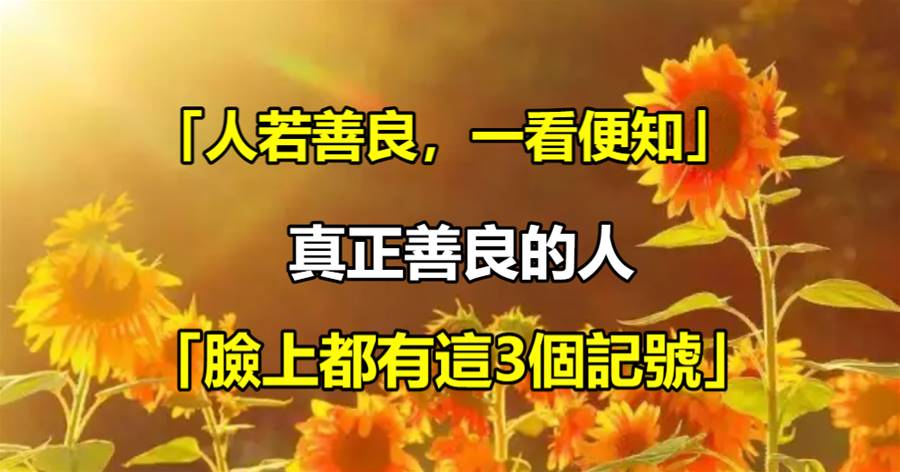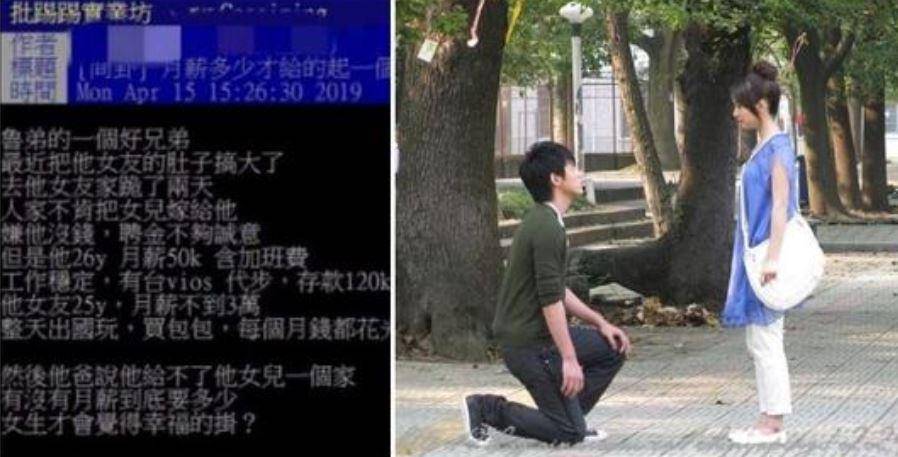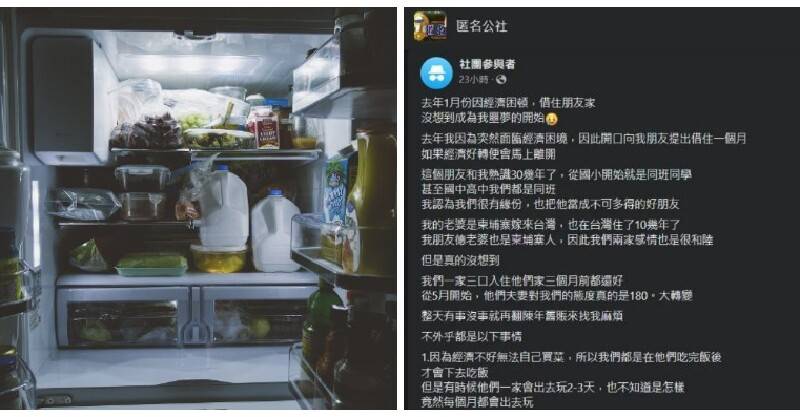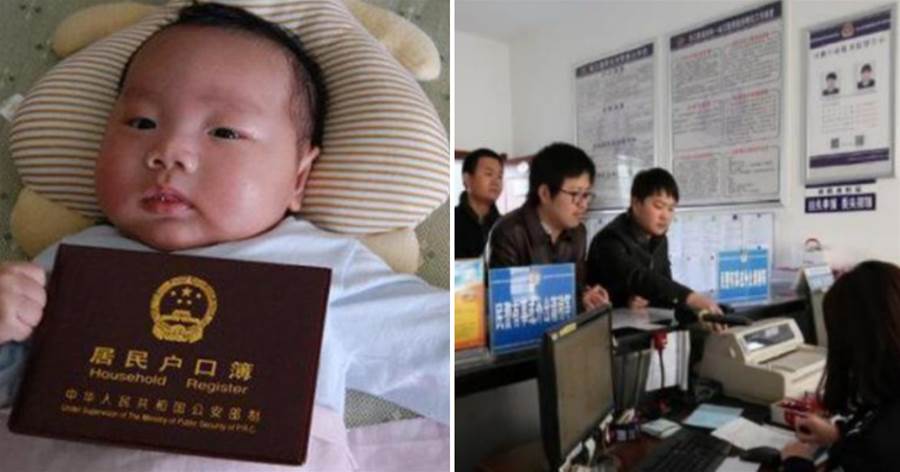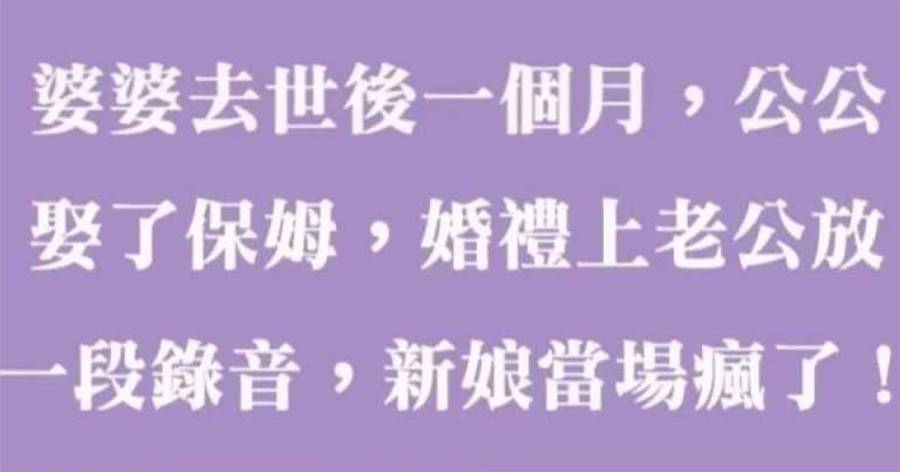我有一個40歲的作家朋友,她總是把亦舒女郎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。
亦舒女郎是那個時代的「港女」,最大特徵:「經濟獨立,精神自由。」
她們不是溫婉柔弱的,希望像男性一樣獨立、理性、擁有成就,婚姻和感情只是錦上添花。
作家朋友也是這麼要求自己的。
二三十歲的時候,她努力寫作,在出版社的工作風生水起,還自己創業辦了文化公司。
但是她發現,亦舒女郎也有不可控的煩惱。
她記得,大概5年前,她迎來了一個事業的高光時刻:
她的第一本書賣得特別好,出版社為她組織了一場盛大的發佈會,請了很多媒體。
發佈會完,慶功宴上,「紅酒剛剛倒進杯子裡,還沒來得及碰杯喝一口」,她就接到了家裡老人的電話。
老人和家裡的保姆起了衝突,幾乎就要有肢體上的碰撞。
電話那頭雞飛狗跳,孩子哇哇大哭,她只能做出一個選擇:
放下酒杯,告訴主辦方家裡出事了,非常不體面地離開了一個原本屬於她的盛大場合。
計程車走到半路,朋友心裡委屈極了,大哭起來:
「我當時就覺得,職業女性的光鮮就像肥皂泡一樣,看著美麗,其實經不起一個針尖的觸碰。
」
「這時候我突然想起來,我先生去哪兒了?當時他在參加一個沙龍活動,而他並不是主角。」
回到家裡,朋友問老人為什麼不給先生打電話,答案是:
「他是個男的,這個應該是你女的來處理。」
外有工作,內有家庭;上要供養父母,下要照顧丈夫兒女。
這就是女人的前半生。

而四十嵗的女人,孩子慢慢長大,事業走向穩定,越來越清楚自己的「定位」;
當我們十幾歲二十幾歲,剛剛走出社會的時候,有太多的未知。
我們不清楚自己什麼,不知道社會什麽樣子;
我們學會養活自己,學會承擔責任,學會在努力和付出中找到自己。
在這個過程中,我們因爲生活的壓力,不得不的迎合別人,委屈自己。
到了四十歲,孩子開始出現「獨立」的想法,想要離開家去長大。
於是,很多姐妹,開始焦慮和彷徨:「孩子怎麽不需要我了?」
感到失落,找不到生活的目標。
但其實,這正是我們第二次獨立的時候。

黨作爲父母的重大使命完成,我們重新做回自己。
不妨重新審視自己的內心:
什麽是自己想要的生活?
什麽是能給自己快樂的東西?
到底自己想成爲什麽樣子的自己?
距離那個目標還需要學習什麽?
甚至是沒有達成的旅行,想要結交的朋友……都可以
不必再委屈求全,不必再八面玲瓏,不必處處忍讓,不必爲難自己;
悅納這個不完美的自己,放開別人的眼光;
回歸自己,讓自己的心靈獨立,不在被外物綁架。
不是很好嗎?

學會給自己的人生做減法,找到自己。
不必成爲成年孩子的幫傭、褓姆,因為那是子女們的責任。
偶爾幫忙可以,但絕不能成為習慣或是責任,否則沒有時間做自己。
因為我們比子女更早老去,生命有限,體力有限,
絕不可能再去承擔他們應該學習的責任。
專心把自己的身體顧好,然後好好去規劃剩下的日子。
無論是追求自己的夢想,還是去旅行,或者做義工、學習……
誠實的面對自己。

打拼了半輩子,四十正是人生的頂峰。
俗話説,月滿則虧,往後的日子,要打算好。
合理的儲蓄和投資,未雨綢繆,是生活最好的保障。
前半輩子,都在尋找自己,並且活在別人的期待裏。
好不容易責任告了一個段落,正是可以做自己的時候;
體力豐沛的第二黃金期也只有短短的 10到 15年,還怎麽經得起浪費?
第二次獨立不是一定要自己終老而活,
而是不再依賴子女,不再活在別人眼光裏
不再對環境有過多的期盼。
明白自己的日子要自己過,自己的快樂要自己負責,剩下的生活自己開創。
我相信當我們把自己活得多采多姿,
就會像吸鐵一樣,吸引兒女想回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