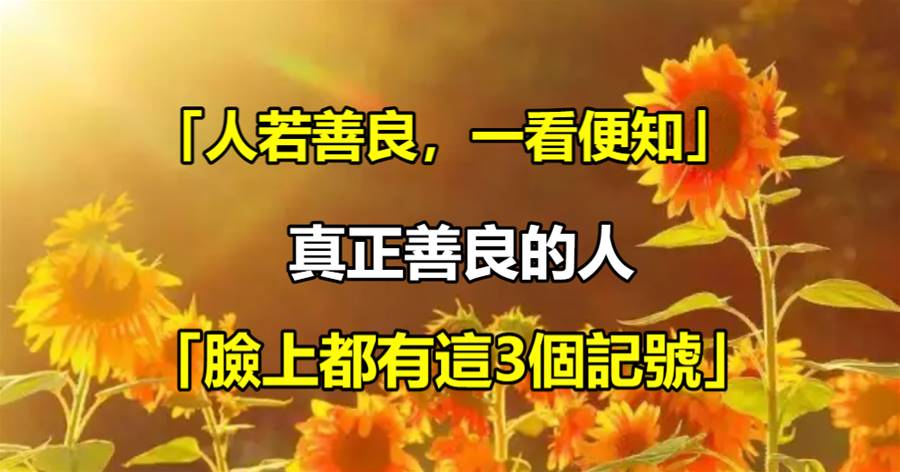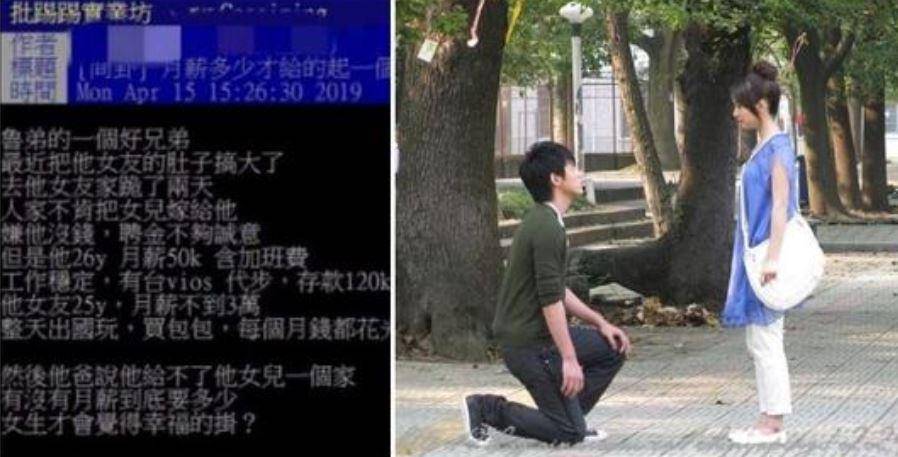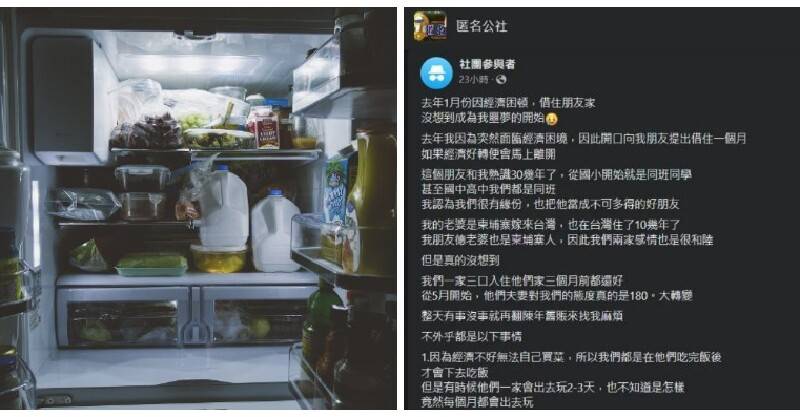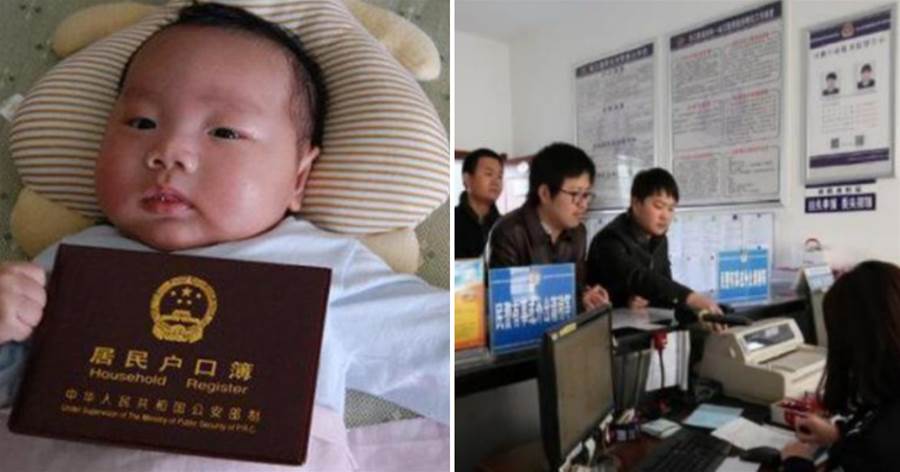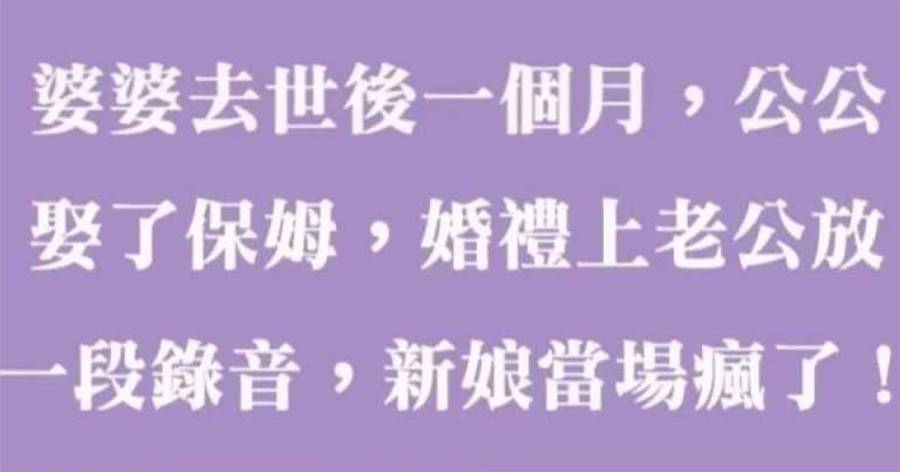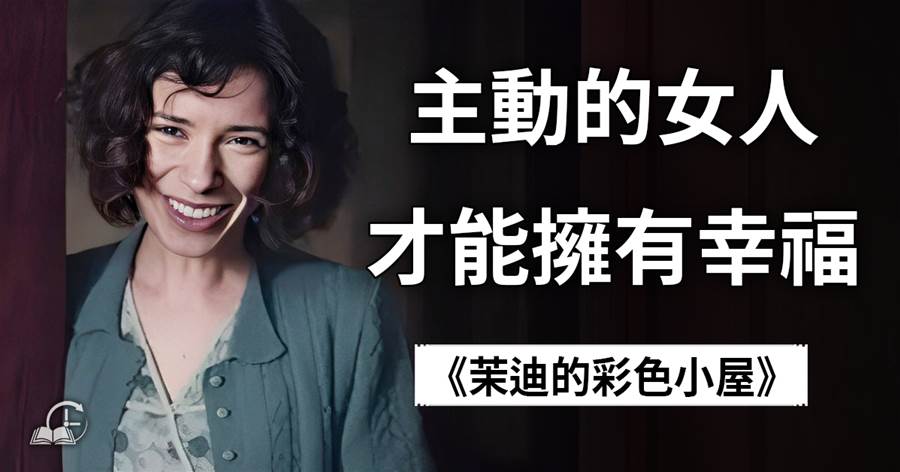

畫畫沒人能教。如果你想畫,畫就是了。——莫娣
近日看了經典電影《茉迪的彩色小屋》,以前看電影介紹的時候,便心心念念,這是個特別的故事,真人真事改編。
實際上電影比我想象的要好。鏡頭隱忍克制,用詩一般的語言去切取生活的片段,平凡中的深刻生命覺知與情感體悟讓人忍不住落淚。
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。這里我只打算從一個平凡女性的角度,去談幾點感受。
主動獲取獨立生活
身體殘障的莫娣被弟弟像丟塊抹布一樣丟給刻薄的姑媽,她下定決心去找工作,為了能當上女傭,她使了點伎倆,把雇主弗雷特的廣告條直接撕走,不給別人留下機會,這成為所有故事的開端。
主動展示自己的才能
莫娣往弗雷特家里的墻上涂鴉,使整面墻都成為展示她繪畫才能的「畫板」,也因此才有機會被前來討「魚債」的女人桑德拉發現她在墻上畫的雞特別可愛,后來成為她的第一個客戶,打開她的繪畫生涯。
主動凸顯自己的價值
弗雷特是個魚販子,身兼數職卻大字不識,經常忘事。莫娣主動幫他記賬,但她說得特別婉轉,讓倔強的弗雷特在不得不接受的同時,對她另眼相看,其實兩人的愛情就悄悄誕生于這種「權利爭奪」的微妙情境中。
主動求愛,收獲一世情緣
她對弗雷特說,他們都不喜歡你,但我喜歡你。
她說這話的時候,弗雷特的內心一定是受到極大震動的。他古怪孤僻的性格和暴躁易怒的脾氣讓他幾乎沒有朋友,也不被人周圍人喜愛,幾乎看不到自己的優點,是個極度自我否定的人。但莫娣看到他身上包括善良、勤勞、溫柔、充滿愛意在內的美好的一切,她用自己的眼光當做燭光,照亮他自身,也溫暖了他冰冷的心。
人們傾向于喜歡喜愛自己的人。弗雷特也不例外,他開始那麼嫌棄莫娣,說她在家里的地位是排在狗和雞后面的,僅位列第四,還當著朋友的面狠狠掀她一巴掌只為了給她一個「教訓」,后來還說她比一條狗還難照顧……
但最后最離不開莫娣的人,是弗雷特自己,莫娣ㄙˇ后,他那落寞的身影,顯示他這一生比從未遇見過她還要更孤獨上百倍千倍,他悲傷得像個深淵。
主動見姑媽,獲知女兒下落
姑媽臨終前想見見莫娣,其實按莫娣之前跟她老ㄙˇ不相往來的性子,打ㄙˇ她是不會去的,但這個女人的決定總是讓人出乎意料。
她一瘸一拐地去了,而且天可憐見,她從姑媽「不想帶著后悔ㄙˇ去」的嘴里,獲知一個驚人的消息:她的女兒沒有ㄙˇ,也沒有畸形,只是被他們賣掉了,如今還活著。
她因為殘障而處處被動,但仔細觀察她的人生軌跡,一切向好都是她主動得來的。這種主動,才是真正具備「大女主」光環的,讓她處處閃耀著人性的光芒。

莫娣其實個性十分倔強,擁有強烈的自尊,她幾次被弗雷特咒罵之后,跛著腳自行離開,那無畏的背影,讓人肅然起敬。
兩個人住一個小屋,睡一張床上,男人想「擁有」她,她提出要求先結婚,他才能完全擁有她,而且認為他們結婚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。
雖然說愛情未必一定要建立在婚姻的「圍城」上,但可以說從這個節點開始,殘障的莫娣和健壯的弗雷特之間的勢能就已經顛倒過來了,弗雷特再也不敢輕視她作為一個女人的情感訴求——她的骨子里從來就不認為自己因為殘障而不配擁有什麼,包括愛情,包括婚姻。而這正是弗雷特的軟肋。從這個角度來說,莫娣要比弗雷特自信得多。
莫娣出名后,連副總統也來信索要她的畫,她要求對方先寄錢過來,否則不賣。甭管你多大人物,在我這里,你就是個買畫的。
他弟弟也想蹭她的名氣,動歪心思過來撈點好處,想做她的經紀人打理她賣畫的錢。
莫娣十分冷靜而克制,既不歇斯底里血口噴人,也不「揚眉吐氣」,但她的「不近人情」說明了一切:她一幅畫都不會白送給他,6美元賣一幅畫給他,然后轉頭把錢遞給自己的丈夫。她很快就跟他說再見,意思是叫他滾蛋,再也不見。
當親情傷害了你,你所能做的,就是守住自己的原則底線,把它干凈地剔除出自己的生活,并不再為此所傷。
如果說一定有什麼是成年女人的保護殼,那保護殼既不是丈夫,也不是那個小屋,而是自己有了獨立生活不被打到的勇氣。管你是副總統還是親弟弟,也不過如此。
婚后幾十年,兩人再次鬧僵到要分手的地步,弗雷特此時才意識到自己如此深愛這個女人,無法失去她。兩人一起坐在秋千上,莫娣說,你看那朵云,像不像一個女人的大屁股?一句話化干戈為玉帛,弗雷特被逗笑了,內心卻淚如雨下。
莫娣三次表達「我很幸福」。
一次在鬧僵后兩人坐在秋千上,一次在臨ㄙˇ前。一次,在她看到仍然活著的女兒后,回家躺床上說:她真美。
莫娣想的是:我的女兒,我一直以為你ㄙˇ了,以為你跟我一樣是畸形的(他們是這麼告訴我的),那一直是我心里抹不去的痛苦。但在我行將就木之際,我看到你竟然還活著,而且健康而美麗,還擁有愛人和美好的家庭,我只是遠遠看你一眼就無比滿足,不求相認。我已經很幸福了。我別無所求。

自古以來,為藝術前仆后繼的人不計其數,為什麼有的人能成為藝術家,有的人卻不能?
莫娣和桑德拉成為朋友,她們兩人在窗戶邊的對話,是整部電影的「靈魂」之筆。桑德拉要莫娣教她畫畫,莫娣卻說:
畫畫沒人能教。如果你想畫,畫就是了。
我哪兒也沒去過,我是依靠記憶來畫畫的。
所有的畫都是我自己的想象。

藝術從哪里來?藝術從來不高大上,藝術是最平凡的生活,因平凡而偉大。藝術源自想象,源自生活里的一扇窗,關鍵是你能從這扇窗戶里看到什麼。
美國傳奇詩人艾米莉·狄金森曾說,「旅行等于閉上眼睛。」她在三四十歲期間閉門不出近十年,在余生的十五年里,也繼續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。和梭羅一樣,她推崇簡樸甚至清貧的生活。
她有一首詩:
因干渴而識水。
因流過的大洋——知陸地。
因痛——知喜——
因傳說的戰爭——知和平——
因紀念儀式——知愛——
因雪,識鳥。
「某種意義上,她重新詮釋了什麼是匱乏,因為得不到——無論是信仰、愛、文壇的認可還是別的欲望——使她具有更敏銳、更深切的領悟力,這是凡事如愿以償的人感受不到的。
」有評論家因此認為,她這緊湊飽滿的意象源自沉思與期許,通過「痛」一陣劇痛——而實現。
當你因為某種貧乏而感到痛苦時,你就知道,應該有艾米莉·狄金森「從匱乏中生出豐裕」的覺知和意志。
作家余華有一句話說,你必須內心豐富,才能擺脫這些生活表面的相似。
反觀到《茉迪的彩色小屋》,莫娣腿腳殘障,一生無法好好照顧自己,她的生活空間非常狹窄,可謂是生活表面極為相似的匱乏的典型。
我們容易對日復一日的生活感到痛苦不堪,也正是因為這種「生活表面的相似」讓人無法忍受。但你完全可以像莫娣一樣,通過自己的熱愛,盡情釋放想象的翅膀,讓它的內在產生本質的不同,這是你可以做到的,至少心境上。
木心說,藝術是要有所犧牲的。如果你以藝術決定一生,就不能像正常人那樣生活了。
我想這話的意思是,如果你仍然按正常人的要求要求自己,那你必然得不到真正的藝術。你自己需要成為藝術,你才能從事藝術。
藝術成為莫娣的避難所,就像科學藝術對于霍金,寫作藝術對于史鐵生,繪畫藝術對于梵高,音樂藝術對于貝多芬……
藝術是最寬容的,它對每個人都敞開胸懷,藝術又是最挑剔的,最終只接納真心擁抱她的人。
藝術是清苦的,如果你連這點都忍受不了,隨便什麼人都能把你從藝術身邊帶走。
藝術又是繁華的,如果你無法欣賞這一點,你將會被表面的貧乏與相似逼到絕境。
萬事萬物都相似,只有你的感悟賦予它與眾不同。
不要奢望誰來拯救你脫離人生的苦海,只有你自己,是一艘倔強的孤舟,當你奮力劃槳的時候,說不定還能順帶將一個人一起送達彼岸。
莫娣從小泅游在孤苦的海上,經歷了許多磨難,因殘障被親人嫌棄、遺棄,自己的孩子也被賣掉,但她敢于反抗,敢于做自己的決定,而且毫無商量的余地,她要憑借一己之力造出一葉扁舟,橫渡大西洋。
在這里,她的「扁舟」,既是她和弗雷特的小木屋,也是她自己創造的繪畫世界——她無限窄小卻異常寬廣的精神世界。她帶著愛抵達彼岸的時候,也帶著弗雷特,因此臨終前,她才一再說:我很幸福。
在我看來,所謂勵志電影,它得具有很深刻的象征意義,每個人都能從故事的存在本身,從對白,從影像畫面,從配樂中,以及從每個細節中讀出自己的故事和眼淚,了解「生活的本質」進而「勇于生活」,再讀出應有的「揚帆起航」的勇氣。
我們無需問生活是什麼。因為我們就是生活本身。每一分每一秒從我們身上流逝的時間,就是生活。如果你痛苦,它就痛苦;如果你快樂,它就快樂。
《古代哲學的智慧》里收錄了蒙田的一句話:
「今天我什麼都沒做。——什麼?難道你沒有生活過嗎?這不僅是你最基本的工作,也是最杰出的貢獻。「
我把它簡化成好理解的模樣: 生活是你最基本的工作,你要把它做好,這工作也是畢生的藝術。
有時候我們總忍不住要把自己的缺陷隱藏起來,企圖把生活的缺陷包裝得鮮艷靚麗,但誰說不是缺陷讓生命更像生命呢?因為生命本身就不完美。